今年的藏历新年和农历春节又遇到一起了。
祝愿我的同族友人洛萨扎西德勒!祝愿各地汉族友人春节快乐!

曾经,我有很多个新年是在藏东康地度过的。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新年没有一个是“博洛萨”(藏历新年),都是农历春节。我亦习以为常,很开心地穿新衣、放鞭炮、吃团圆饭、领压岁钱。我记得,在“达折多”(今四川省甘孜州康定),从初一到十五,亲友们相互拜年,轮流安排聚餐,但这样的新年不是藏历新年。
回到拉萨后,才开始过“博洛萨”,才知道为了迎接“博洛萨”,在这之前就得培育青稞苗、做青稞酒、炸“卡赛”和“桑冈帕勒”(用酥油炸制的各种点心)、准备“竹素切玛”(五谷斗)和“鲁过”(以酥油花雕塑的羊头)。
藏历新年的种种习俗
藏历1月29日的晚上,家里要做很美味的“古突”(面疙瘩汤),还要很好玩地察看每个人喝的 “古突”里包的是石头、辣椒还是羊毛、木炭(我竟然连续几年吃到的都是盐,据说这意味着懒惰),然后要进行驱鬼的仪式。每次驱鬼,我都要被家里派去倒掉那象征鬼的东西。那其实是一些糌粑捏的块儿,我们把它在身上摩娑几回,嘴里要说,所有的晦气啊霉气啊病气啊都快快离开吧,不要再来了。然后扔在一个盆子或盒子里,在火把的指引下,一路放着鞭炮,一口气冲出家门,径直奔向一个十字路口扔掉它。
藏历1月30日的晚上,要在家里的佛龛跟前供放层层叠叠的“德嘎”(油炸面供品)以及茶叶、酥油、糖果、盐巴、“鲁过”、人参果、青稞酒、青稞苗等等,要给佛龛和所有的唐卡换上崭新的哈达,而我会穿上拉萨式样的藏装、带上哈达和酥油灯,代表全家去大昭寺,在初一的零点时分,面向金壁辉煌的释迦牟尼佛像伏拜三个等身长头,然后朝拜每一座佛殿。对于我来说,这渐渐成了属于我自己的习俗。对了,初三是要登上房顶换“塔觉”(经幡旗杆)的,如果能请到穿绛红袈裟的僧侣来家里诵经祈祷更是幸运不过,然后去城东的朋巴日(宝瓶山)或者城中的夹波日(药王山)顶上挂经幡……
过去,还要在大昭寺举行整整21天的祈愿大法会——“默朗钦莫”,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以及其它寺院的数万僧人云集于此,举行修法、辩经、驱魔、酥油花灯会、迎请未来强巴佛等盛大活动,但文革发生那年被当作“四旧”给取消了, 1986年恢复,1989年又被取消,至今再不举行。
藏历、中国农历两套文化系统
西藏的历算简称藏历,中国的历算通称农历。且不说藏历、农历与现今世界通用的公历并不相同,就藏历与农历相对照也不一样,所体现的是两种独特而完整的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
对于习惯用公历来表示时间的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藏历还是农历,其作用远不如公历重要,因此藏历与农历的明显区别往往表现在年节上。藏历新年和农历春节在时间与仪式上,其实有着各自不同的推算方法和传统习俗,其中蕴含的是由此得以凝聚和延续的民族认同等意识。
然而,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藏族学者所调查到的:“藏民族传统的藏历年,已经在广大青海藏区渐渐衰落乃至废弃,藏族民众日益转向了、并开始注重起春节的庆贺。”他还说,“随着汉文化势力逐渐向更西部蔓延,作为国家统一文化思想标志的春节庆典…… 日益影响并取代了青海其它各族相当于年终庆典的民俗活动。由此,春节逐渐下渗进民众的日常生活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霸权’。”
2006年藏历新年期间,我曾在我的博客上讨论过有关年节错位的话题,一位安多(今甘肃、青海、四川的大部分藏地)学子的看法是,“其实藏族的民俗力量还是很伟大的,甘青的安多、康巴藏区的年节错位是历史环境、地理环境、气候环境造成的,但其中的年庆氛围是纯藏化的”。话虽这么说,然而毕竟在这些藏地,藏历新年被农历春节替代已是事实。既然明白这是错位,为何就不能逐渐复位呢?
一位朋友发来mail说:“在中国,藏人和维吾尔的民族主义者大都是在民族学院学习过、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工作过的;离开他们的文化,土地很久的人”,这句话让我警觉并且反省自己。
对于如我这样一个其实基本上离开“文化,土地很久的人”,需要的是回到“文化,土地”之中,去切实地经历和体验每一个日子,当然如果能够像每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人和牧人那样去切实地经历和体验每一个日子,那才可以对“文化,土地”发言,但我深知这是非常困难的,毕竟我今生今世已经不可能化身为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人和牧人了,只能是、今后也必须时时注意的是,——换位思考的角度。这应该是起码的。
不过,之所以纠缠于“节日”这个话题,朋友信中的这句话可谓道出了我的用意:“现代人庆祝节日的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确实是这样。换句话说,每个民族以及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存在,都必然与自己所生存的土壤相适应,正如农历在东亚不限于中国,就安多和康而言,如果农历春节比藏历新年更适合自己的土壤,倒也不存在错位或者复位之说。就像如今在境外的藏人流亡社会,每年的雪顿节已不是传统藏历上的雪顿节,而有了重新的调整与安排,这表明新的雪顿节更适合自己所在的新土壤。
自己选择非強加就合情合理
但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此。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我想我应该把这句话说出来,——只要是自己决定的,只要是自己内部的民众决定的,就是无可非议的,就是合情合理的。换句话说,当包括卫藏(今西藏自治区的主要藏地)、安多和康(今四川、云南和西藏自治区的藏地或部分藏地)在内的西藏实现了高度自治,无论是过藏历新年也罢,还是过农历春节也罢,甚至以西方人过圣诞节的方式来迎接新年也罢,那都毫无任何不妥,反而呈现出多样化的丰富意义。可是,在如今这样一种并非真正自治的体制下,西藏民族的文化不断被侵袭、被污染、被改变,会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上,比如年节的错位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而这样的细节随着年年月月的堆砌,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是像来自安多热贡的年轻藏人在朝拜大昭寺时,因为被拉萨人视为来自“卡切隆巴”(回族居住的地方)而“没有支配能力地哭了”?还是像达赖喇嘛给一个海外华人讲的寓言:“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后,有一个婆罗门会看相。他看出释迦牟尼未来会成为拯救人类的导师。但他自己却哭了。他说:佛祖会完成他的伟大事业,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
记得2006年的藏历新年和农历春节相差一个月,可是在拉萨的春节除夕之夜,满耳是全城的爆竹频传,满目是全城的火树银花,当时我心里只有这样的疑问:“有多少分布于城中各处的人们正在齐辞旧岁?他们是拉萨本地人,还是五湖四海人?”
在这个农历春节的除夕之夜,难道,在拉萨,已经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过春节的移民或短期移民吗?那天晚上,央视春节晚会上零点时分的钟声尚未敲响,拉萨全城的鞭炮声已经震天响。我奔上屋顶四周观望,啊,一道道飞腾的焰火照亮星月无多的拉萨夜空,使得宛如舞台布景的孜布达拉闪闪灭灭。
这着实令人惊诧!
居住在华盛顿的好友卓嘎告诉我,每当藏历新年来临,周围的藏人们都会按照传统的西藏习俗度过新年,培育青稞苗、做青稞酒、炸“卡赛”和“桑冈帕勒”、准备“竹素切玛”和“鲁过”……而这一切,过去她在拉萨的家里并不擅长,那都是属于长辈的家务,但如今她和周围的并不年长的藏人们个个都会。“博洛萨”期间,他们挨家聚会,品尝着卫藏、安多和康的饮食,吟唱着卫藏、安多和康的歌曲,交谈着卫藏、安多和康的方言……在“博洛萨”的日子里,就这样度过了“博洛萨”。
二○○八年北京
——《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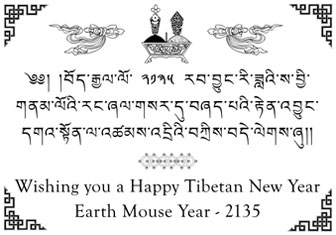
Comments